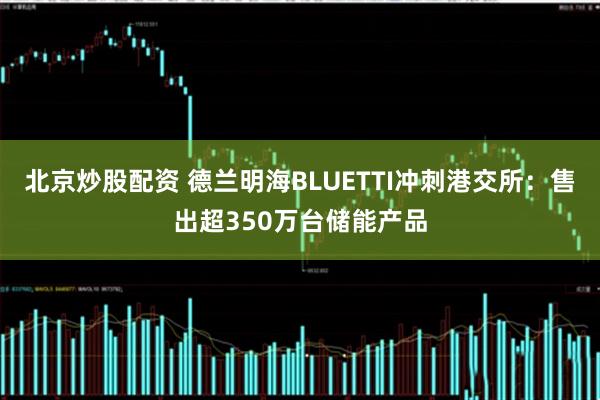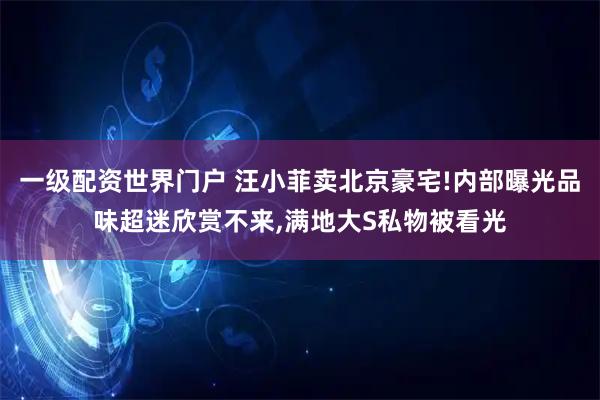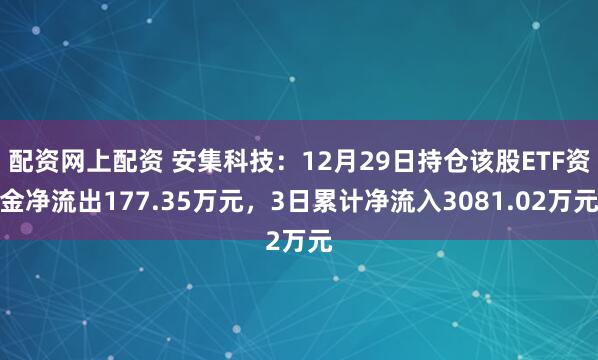"老虎吃人有躲闪,人吃人可没躲闪啊!"1980年秋天,陈永贵坐在北京交道口的小院里,说出了这句让人心头一紧的话。这个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农民副总理,此时满脸的无奈和沧桑。
政治风暴中的无奈
那天下午,从山西来的人告诉陈永贵一个消息。山西省人大开会了,一群代表对着他狠批一顿,还要撤掉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。有人甚至提出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
陈永贵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院子里的梧桐叶子正黄,秋风一吹哗啦啦地响。他想起两个月前自己还是副总理,虽然已经主动辞职,但没想到会有人这么急着要"清算"他。
那些在山西攻击他的人里头,有不少是他以前提拔过的干部。大寨红旗飘扬的时候,这些人对他点头哈腰的,现在风向一变,立马调转枪口。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跟陈永贵划清了界限。
幸好还有领导出面压住了那个罢免提案。有关领导说得挺实在:"下次不选就行了,罢免就算处分了,不好。"虽然保住了最后一点颜面,但这话也透露出一个信息:他陈永贵在新的政治格局里,确实没位置了。
展开剩余91%坐在那个简陋的小院里,陈永贵的思绪飘得很远。从1975年当副总理到1980年辞职,短短五年,他就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跌到了谷底。这个曾经被誉为"农民政治家"的山西汉子,现在尝到的是政治最苦的滋味。
那些为大寨奋斗的日日夜夜,全国各地来学习的参观团,外国政要对大寨精神的赞叹,这些荣耀仿佛还在昨天。可现在却成了别人攻击他的把柄。一些人编造谎言,搞"揭发材料"送到中央。
最痛苦的不是这些攻击,而是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大寨精神,也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被践踏得面目全非。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经济林砍了种庄稼,说这是学大寨。有的地方把平展展的耕地改成梯田,也说这叫学大寨。
大寨人千辛万苦修建的梯田,是因为没有平地才不得已而为之。可有些人生搬硬套,把学大寨变成了形式主义的闹剧。
"老虎吃人有躲闪,人吃人可没躲闪啊!"这句话成了陈永贵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感悟。在政治的丛林里,有时候人性比兽性更冷酷。野兽只是为了生存,而人却可能为了利益、为了表态、为了自保,做出更冷酷的事情。
改革春风冲击下的大寨衰落
陈永贵的这句感慨不是空穴来风。从1978年开始,一股强劲的改革春风就冲击着以大寨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模式。这股风最初只是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的红手印,但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。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长期存在的"一大二公"、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,摈弃了平均主义和吃"大锅饭"的分配办法。这种新的生产方式,与大寨强调的集体劳动、统一管理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1978年12月2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封来信。写信人自称"陈灵风",来自山西,矛头直指大寨。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"胡乱吹",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,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,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,是"国家出钱,农民种田"。
这封信的刊登,标志着大寨模式从神坛上跌落的开始。在此之前,批评大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可现在,连《人民日报》都敢公开刊登质疑的声音了,说明政治风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更要命的是,这种批评不是毫无根据。根据山西省统计局的核算,昔阳县自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间,共虚报了粮食产量2.7亿多斤,比实际粮食产量多报了近24%。这个数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,彻底炸碎了大寨"高产典型"的光环。
1973年秋天,长达一个月的阴雨天气,使得昔阳全县粮食歉收。陈永贵刚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。为了抵消政治影响,山西地方配合上级指示,各级单位层层多报谎报。1973年的实际粮食产量为1.39亿斤,上报调整到2.39亿斤,比实际产量多报了1亿斤。
大寨作为全国样板,政治上不能减产。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,只能以73年的账目为基础,继续虚报,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77年。虚报成了一种惯性,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。
与此同时,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。包产到户后,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,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增长。相比之下,大寨那套集体劳动、统一分配的模式,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。
陈永贵对这种变化是抵触的。他始终认为,只有集体化道路才是农村发展的正确方向。可现实却给了他响亮的耳光。那些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,农民收入明显提高,生活水平显著改善。而坚持集体化的大寨,反而显得死气沉沉。
更让陈永贵心寒的是,有些人以为他要垮台了,也来了个"落井下石",编造谎言,攻击诬陷,搞"揭发材料"送到中央。这些人中,有不少曾经是大寨模式的受益者,现在却急于撇清关系。
舆论的风向也在悄然改变。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等主流媒体连续发文批评大寨模式和大寨的增产数据问题。那些曾经大力宣传大寨精神的记者,现在却成了批评大寨的急先锋。
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再也不要干"西水东调"式的蠢事了》,甚至还攻击大寨说,它不是干出来的,是国家喂起来的,还用秦始皇修长城、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。这样的批评让陈永贵气得吃不下饭,身体也因此垮了下来。
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,随着他个人命运的起伏,已经接近完工并且使大部分社队受益的昔阳"西水东调工程"也被迫中止。这个工程已经开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,只要再建一座水库,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。可现在,因为政治风向的改变,这个造福人民的工程也被贴上了"劳民伤财"的标签。
在病床上,陈永贵唉声叹气,念念叨叨地说:"实事求是,实事求是。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,咋成了蠢事?昔阳没武斗、没停产、经济飞跃,咋成了重灾区?大寨苦干了多年,咋倒欠了国家的债?"
这些问题,陈永贵想不通,也问不出答案。在历史的洪流面前,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。即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,也无法阻挡时代变迁的脚步。
从农民到副总理的传奇
人们总说命运弄人,但有时候命运也会成就人。陈永贵的后半生轨迹,恰恰印证了这个道理。1948年,当这个三十多岁的山西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,谁也不会想到,二十多年后,他会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,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理。
1952年,陈永贵接替"主动让贤"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大寨大队支部书记。那时的大寨,真的是穷得叮当响。用当地人的话说,就是"七沟八梁一面坡"。放眼望去,全是石头山,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山沟里,不仅面积小,而且土质贫瘠。
很多人看着这样的自然条件,都觉得没戏。可陈永贵偏偏不信这个邪,他相信人定胜天,相信只要肯干,就没有改变不了的山河。
他们凭着扁担、箩筐、锄头、铁镐,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,平整田地,蓄水保粮,抗旱防涝。1952年亩产237斤,1962年增至亩产774斤。这个数字看起来可能不算啥,但在那个年代,在那样的自然条件下,能够实现产量翻三倍,简直就是奇迹。
改造大寨的过程,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,全靠人力。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拿着最原始的工具,在石头山上一锄头一锄头地刨,一担土一担土地挑。夏天顶着烈日,冬天冒着严寒,就是要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,造出能养活全村人的良田。
陈永贵这个人,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。别人说不行的事,他偏要试试。别人觉得没希望的事,他偏要坚持到底。每当遇到困难,村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,总是陈永贵站出来,鼓励大家继续干下去。
真正让大寨声名远播的,是1963年那场特大水灾。8月份,大寨遭受特大暴雨,冲垮100条大石坝,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,冲塌了113孔窑洞,倒塌房屋77间。灾情严重,但大寨人没有气馁,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、救济粮、救济物质,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,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。
陈永贵望着被毁坏的村子暗自咬牙,行动上却呵呵直笑拱手给各位乡亲道喜。大家边哭边问,成了这样有啥可喜的?陈永贵解释说:这事如果放在解放前,住那土窑洞,咱们都得被淹死压死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好好的啥事没有还不值得道喜嘛?
大寨村对全体社员宣布:大灾之年,不要救济物资、不要救济粮、不要救济款。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、群众口粮不少、上交国家公粮不少,当时称为"三不要"和"三不少"。这种表态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,可大寨人真的做到了。
消息传到北京,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。新华社记者把大寨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《大寨之路》,在1964年2月1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头版上刊发,并配发了社论《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》。
毛泽东在听了山西省委书记汇报后高兴地说:穷山沟里出好文章。1964年12月21日,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,周恩来总理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专门表扬了大寨,他把"大寨精神"总结为八个字: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。
从这时候开始,"农业学大寨"的口号响彻全国。轰轰烈烈的"农业学大寨"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。陈永贵也从一个普通的村干部,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业劳动模范。
随着大寨名气的增大,陈永贵的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升。1975年1月,陈永贵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,并史无前例地从上到下同时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共晋中地委书记兼昔阳县委书记兼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。
这种身兼数职的情况,在中国政治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。一个人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村党支部书记,听起来就很有戏剧性。当时副总理的工资为每月400多元,陈永贵不领工资,只挣在大寨的工分,无法承担伙食费,所以政府另行补助他每月120元"生活补贴"。
他请求在工作期间以1/3时间到全国调查、1/3时间回大寨务农、剩余1/3时间留在中央工作,受到毛泽东的批准和肯定。即使当了副总理,他也不愿意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。
苦难童年铸就的钢铁意志
要理解陈永贵这个人,就必须回到他的童年。一个人的性格和价值观,往往在童年时期就基本定型。陈永贵后来表现出的那种顽强不屈、永不服输的精神,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那段充满苦难的童年经历。
关于陈永贵的出生年份,一直有争议。他自己对出生年月也从没弄清楚过,不知是出生在头一年冬,还是第二年春。按照农历,他给自己定为正月初一,那是一个好日子。这是苦人图的吉利。连自己的生日都搞不清楚,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,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却是很常见的事情。
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距大寨不过5里的小南山村,一家5口都过着贫苦的生活。在陈永贵6岁之前,哪怕生活贫困,一家人辛勤劳作也能勉强吃饱。但陈永贵6岁那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让当地粮食颗粒无收,百姓饿死无数,多有为了活命卖儿卖女之事发生。
这场灾荒对陈永贵一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陈永贵作为长子得以保全,而他的母亲、姐姐和弟弟则都被父亲卖掉了。一个六岁的孩子,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、姐姐和弟弟被父亲卖给别人,这种心理创伤无法想象。
陈志如用箩筐挑着陈永贵,父子两人一路流浪到了大寨,一处破窑洞成了他们暂时的落脚之处。从小南山村到大寨,虽然只有五里路,但对于这对父子来说,却是从一个绝望走向另一个绝望。
陈永贵出身贫农,6岁时随父迁居大寨。不久,陈父自缢身亡,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。后来陈永贵认一位寡妇为干妈,寄养在其家中,小小年纪就给人放牲口,打短工,扛长工,有机会还到饭铺当了学徒,做起了小买卖。
一个六七岁的孩子,就要承担成年人的劳动,这在今天无法想象。可在那个年代,这就是穷人家孩子的宿命。陈永贵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,学会了在艰难困苦中求生存。
1940年,昔阳又迎来了新一轮灾荒,陈志如自觉走投无路,吊死在了石山祖坟一棵大树上。26岁的陈永贵自此失去了所有亲人。父亲的自杀,对陈永贵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两次类似的痛苦体验,让陈永贵对粮食增产有了强烈执念。
这种"强烈执念",后来成为推动陈永贵改造大寨的根本动力。他深深地知道,没有粮食意味着什么。饥饿不仅会要人的命,更会击垮人的尊严,会让父亲卖掉妻子儿女,会让男人走上绝路。
陈永贵从未受过正规教育,属于半文盲。因为看不懂秘书代写的演讲稿,政府专门派人为陈永贵特制了一种行距奇宽的稿纸,一页只能容纳一百个字。通篇用"大白话"撰文,较复杂的字全部都用同音字注音。
可陈永贵虽然没有文化,却有着朴素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。他能凭借自己的天赋,创作出很多与农业有关的"打油诗"。他的那些朴实无华的话语,往往比那些华丽的辞藻更能打动人心。
昔阳在20世纪40年代就得到了解放,陈永贵也经土地改革分到了一定的土地和房屋。对于一个从小就饱受饥寒之苦的人来说,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,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
1946年,他带领4老6少组成了"老少互助组",经过一年苦干,在一众小组中拔得了头筹,实现了当地最高的粮食亩产。经过近两年的观察和考核,1948年,陈永贵被介绍进中国共产党。
从1914年出生到1948年入党,陈永贵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从一个苦命孩子到共产党员的转变。这期间,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痛苦,体验了寄人篱下的屈辱,也尝到了自力更生的甜头。所有这些经历,都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,塑造了他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
童年的苦难,没有击垮陈永贵,反而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。那种对土地的深厚感情,对丰收的强烈渴望,对自力更生的坚定信念,都源于他那段充满苦难的成长经历。正是这些品格配资吧官网最新信息,让他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,能够创造出大寨这样的奇迹,也能够在政治风云变幻中,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。
发布于:河南省富明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